|
厚 土
杜怀超
作者简介:杜怀超,男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在《散文海外版》《雨花》《四川文学》《朔方》《延河》《青海湖》《安徽文学》《鸭绿江》等几十家纯文学期刊发表散文、小说百余万字;中国江南“言子文学奖”获得者;长篇系列散文《一个人的农具史》获2010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,2011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。
1.
在场的人无不为之落泪。
当劳爷头一挨到拾边地时,麻绳编织的凉床发出欢叫的声响,似乎是呼唤劳爷的声音。也许在每一个旁观者看来,这声音在普通不过了,两块木头相互挤压的声音最多不过是一种疼痛,瞬间从心上划过去。然劳爷则从疼痛中惊醒,手一触摸到久违的庄稼,久久沉睡的他似返青的青苗,立马回到勃勃生气的春天里。
劳爷挣扎了几下,还是弓着身子坐了起来,接着又颤颤巍巍地披上红红绿绿的衣服。劳爷在衣服的颜色上停留了几秒,仅几秒而已。这颜色他懂,不就是送他去天堂的衣服?无所谓了,有庄稼在身边,哪里不是他的天堂?劳爷接过不知道谁递过来的布鞋,慌乱中穿上了脚,一只还半拖着,后跟没有拔上,就这么撒着。对劳爷来说,看到他的大豆、山芋、高粱这些他的子民们,就已经足够了。
劳爷趴在山芋墒间,一只手摸索着山芋秧,对着碧绿厚实的叶子,脸上的笑容开了花。肥硕的叶子,叶脉也是粗壮的,似乎道道小溪正从大地的深处欢快地汲取着营养,汩汩流淌的声响,奏起动听的音乐。劳爷拽着一根藤叶,使劲地凑到鼻子边嗅了再嗅,生长的气息沁入劳爷的心脾。劳爷又走到一片豆地,挤挤挨挨的豆苗泼皮着呢,别看他们矮小,可棵棵壮实着呢。虽未到秋季,可是有些早熟的豆苗开始孕育小豆豆了,肚皮鼓鼓地,好似跟谁赌气似的,要不,就是想在劳爷面前显摆着呢。劳爷,您瞧,我长得壮壮的呢!不信,您老摸摸?说着故意把肚皮再鼓了鼓。劳爷笑嘻嘻的样子,似乎听懂了豆子说话的声音,竟摘下还没有成熟的豆荚,剥了皮,把幼小的豆粒送到嘴里,砸吧砸吧着,那神情陶醉极了。唯有那长得高大挺拔的高粱,不解风情地,顶着一头火红的光芒在月光下燃烧,也好像和劳爷攒劲似的。劳爷,嘻嘻,您就是够不着我。劳爷没有在意高粱调皮的笑声,自言自语道,高我就怕你了啊,小崽子,看我怎么收拾你!劳爷把手伸向高粱的根部,使劲地晃了两下,高粱发出阵阵惊呼,劳爷,你来真的啊!劳爷听到呼喊,立马住手,那只手就保持着抚摸的姿势伸向半空中,整个夜空都是庄稼的影子。
劳爷常带领儿女们在月亮下耕种。劳爷和儿女们交流的时候,劳爷总是告诉他们,那不是星星,是庄稼人把种子种在了天上,等着我们把他们摘下来种到地上呢。劳爷是个典型的庄稼好手,方圆十里,无人不知。人家一亩地能产一千斤水稻,而他摆弄的稻田总能产一千两三百斤。劳爷有时还神神道道地说,要是他种地再好些,就能到天上去耕种呢?你们看,那月亮不就像他手里的那把锄头,正在锄田间的杂草。人勤地不懒。你给田地多少血汗,泥土就给送来多少粮食呢。
水!水!水!劳爷突然惊叫。
众人赶忙把矿泉水递到劳爷的嘴边。劳爷就拼命地摇头、摆手。不是,不是的。劳爷有点怒吼道。声音洪大,似乎吹皱起了河畔波纹,清澈的河水在白银的月光里,缓缓地流淌,它哪里知道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在梦中呼喊它的名字。
儿子劳力走上前去,顺着爹的喊话,问道,水?什么水?劳爷还是念叨着,水!顺着劳爷手指的方向,儿子看到了有片田地已经张开了干旱的口子了。
儿子明白了劳爷的意思,浇水?劳爷点了下头,嘴哆哆嗦嗦着。
儿子就纳闷了,还浇水干什么?劳力看着四围的变化,他觉得有些不必要这样做了。不远处,脚手架林立,似乎突然间从泥土之下冒出的森林,转眼参天耸立。庄稼也大片大片地消失了,在与城市的抵抗中溃败乃至销声匿迹了。现在,在城市的空间里,能找到块像样的庄稼地已不寻常了。身边,还有片巴掌大的土地,上面种满了庄稼。
儿子问劳爷,还浇?
浇!劳爷晃了晃身子,一下子歪倒在田地里。众人一阵唏嘘。劳爷还惦记着这块地呢!
2.
听到拆迁的消息,已近古稀的劳爷就有点郁郁寡欢了,终日在那块巴掌大的拾边地上劳作。拾边地,也就是河边的荒地而已,劳爷看着荒了可惜,利用几个半天把它耕作一番,后栽种上了蔬菜或者农作物,冬季到来就种上麦子、油菜之类,夏季来临就种上大豆、玉米等,在沟埂上,劳爷还见缝插针,种了点山芋、西红柿,还有丝瓜等青货,长势喜人。
儿子劳力深夜找来,劝劳爷回家,爹,你瞎忙什么东西啊?有什么用?推土机说来就来,你这小地还有命?拆迁办的通知已经都告示好久了,你还留念个啥?劳爷没有理睬儿子,拿着水瓢,给萝卜秧子浇水。趁着丝绸的月光,那从汴河里才担上来的碎银般的水,拌着月光流进萝卜秧子的根部,直抵达植物的命脉。劳爷看着周围泥土慢慢湿润,心也跟着滋润起来。栽菜浇瓜,不能心急,否则的话,瓜秧、蔬菜等之类等到朝阳升起来,准会被晒死的。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些植物的周围,挖个洼地,水就倒在这片洼地里,然后慢慢地洇进植物的根部,不旱不涝,给植物输送持久的水分。
劳爷今个不想和儿子探讨这个问题,再说儿子他一贯不感兴趣,简直是对牛弹琴。有时候劳爷想,劳力是不是他儿子?一谈到种地,就有深仇大恨般,死活不愿意跟他学种地。兔崽子的,没有土地,早就给你饿死了。人啊,不能忘本啊!儿子天生的叛逆,不买劳爷的帐。劳力说,爹,不要再翻您那老黄历了,不就您老是种庄稼的能手?方圆十里,谁个不知?名气大呢。可啥用?还不是穷一辈子?劳爷一想起着,就痛心疾首的样子。劳爷生气了,就会冲着劳力说,你个龟种的,你以为你是城里人哪?你看你整天烧得不得了……
劳爷一家住在乡下,可近两年由于房地产业迅猛发展,使原先大片大片的庄稼地被蚕食了,取而代之的是摩天的高楼。劳爷一家由原先的乡下人,逐渐蜕变成了城郊人,在城市与乡村的缝隙间生存。最有明显标志的是,到今天,劳爷一家还保持着农耕的方式,家里的叉耙扫帚、犁铧镰刀一样不少。准确地说,他们一家是城市里的农村人。不幸的是,招商引资的风暴再起刮起,席卷到劳爷家,上面带人来考察景致,看中了劳爷家周围的地方,更准确地说,看中的是劳爷家门前的那条历史悠久的河流。
儿子不买老子的帐,不是城里人咋地啦?商品楼房一起来,咱买上一套,咱家就是标准的城里人。刮风下雨,咱们也能走在水泥马路上,再也不走那烂泥地了。
切,瞧你个烧包样子,拿鸟钱去买啊?
人挪活,树挪死。你怎么还抱着一亩三分地忙活呢?
瞎忙。儿子劳力的话语重了点。
劳爷一听,双眼睁圆,小狗崽的,你个不吃粮食的,种地怎么了?天下都不种地,都去喝西北风啊?
说着劳爷扬起手里的水瓢就要掼儿子,但手明显地软了下来。
俄顷,劳爷叹了口气,看看周围,拆迁的拆迁、租房的租房,原先的人家几乎都走光了。不远处,开发商的售楼处已经动工了,一处名曰帝豪度假村——都市化、国际化的高级商业化住宅小区开始走进小城人的生活。马路上,车辆穿梭,比泥土里的甲壳虫还多,密密麻麻地,喇叭声不停。劳爷有时恍惚,难道自己真的落伍了,这世道真的不再需要种地?没有土地,我们到底吃啥?
劳爷想不通。房子拆迁了,可是劳爷又在河边搭了个庵棚,继续驻扎。工地上的人来过这儿好几次了,老人家,怎么还没有搬迁啊?舍不得啊。劳爷陪着笑容,就搬,就搬。在这河岸上住了几辈了,乍走真的舍不得啊。劳爷整天好象丢了魂魄似的,白天薅草,夜里就去河里担水浇那菜地。一夜,两夜,三夜……都快半个月呢。周围的菜地、庄稼早已一片狼籍,惟独这块地鲜嫩着呢。
劳爷弯着腰,一瓢一瓢,给菜地里的黄瓜、茄子以及葱啊蒜啊们浇水,婴儿般地喂奶,惟恐哪个孩子少吃一顿、少喝了一口。他每浇一棵,身体就笨拙地移动一块屁股大的地方,沿着墒沟继续前行。
七八十岁的人哪,还犟脾气。
爹,睡觉去吧,净做些无用的事。劳力又唠叨了一句,这费用开发商不是早就补过了吗。
钱,钱,你就知道钱,都走了,这庄稼还怎么活?它也是有命的啊!
要走你走,我不走。
劳爷头都不抬。
3.
天刚蒙蒙亮,劳爷就起身了,扛着锄头,火急火燎地往那拾边地去。昨天夜里回来,他扳着手指头算了好几遍,该给山芋培土了。山芋很有脾气,土要喧松,垄要饱满。你给它多大的垄,它就能长出多少山芋来。眼下山芋已经长出好多片叶子了,即将长出小山芋呢,可马虎不得。俗话说,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季呢。
劳爷怎么也想不通,住在这河边好好的,干吗要拆迁呢?说是盖房子,这房子不是好好的?高楼?与平房有什么区别?上楼下楼,还不把人累坏?一家两家,对门却老死不相往来。哪如咱这,东家老太招呼一声,大家三五个凑在一起,说个家长里短,多爽心?看那长高的楼房,怎么看怎么像鸽子笼似的,人成了不会飞的鸟了。这庄稼人,泥土命。人一登上了高楼,不是脱离了泥土么?那还有命?和庄稼失去了泥土有什么两样?
人啊,活到最后,也就是一棵会走的庄稼啊!劳爷深叹一口长气。从泥土里刨食,到老来终究还是要回到泥土里,那才是最终的家。劳爷自言自语,等他老了,他才不愿意去那烟囱里走一回。
太阳升起一竿多高了,晒得人头直发昏。劳爷有点累了。咋不是的呢。他已经足足干了三个多钟头了,还是舍不得离开这儿。昨会舍得呢?这是劳爷最后的土地了。从无边的旷野走来,在城市的蚕食下,土地越来越瘦了。在泥土上侍弄半辈子的劳爷一家,活得越来越不像个农民了。没有土地的农民还是农民吗?失去土地的劳爷有过疯狂的往事——翻墙种地。河对岸有片围墙,墙内不知何时圈走了大片庄稼地,上百亩的土地呢。劳爷偶然间发现,唏嘘不已。一年,两年甚至第三个年头,这块地还是没有动静。劳爷急了,庄稼地不种庄稼,是要遭天谴的。劳爷决定偷块地种种。结果春天来临,土地的主人把劳爷的庄稼一毁干净,疯狂的野草密布上面,庄稼地也就不是庄稼地,成了荒地。后来劳爷还是找到了块拾边地,继续春种秋收的日子。
儿媳妇翠花拉着娃子走过来。
爹,回去吧。翠花望着爹。您种了一辈子地,还没有种够吗?也该享享清福了。劳爷望了眼孝顺的儿媳妇翠花,嘴角有点暖意,没有言语。翠花是个老师,能说会道。的确,再难再苦,就是种地人。一季季的庄稼,全靠老天吃饭,狂风来了,麦子倒伏了;暴雨来了,稻穗砸落了,干旱来,禾苗枯死了……劳爷想想自己汗水摔八瓣,养活了三个娃,不觉得鼻子辛酸。大儿子、二儿子大学毕业后,就留在了北京。只有小儿子劳力留在身边,依靠自己的能力,自己在小县城创办了个小公司,生意还不错。
翠花继续劝说,城市发展了,盖高楼是好事呢。爹您想啊,下雨天上个街买个菜都很方便,菜市场到处都是,什么菜都有,就连您老喜爱的山芋一年四季都有呢。还有,早晨起来,您要是不喜欢在家吃,还可以到街上吃早点嘛,那可有滋味呢。再说,这房子拆了,地没了,政府也会给咱们新房子的。咱种半辈子的地了,现在不种也算对得起土地了。劳爷被儿媳妇说得心思有些松动,眉毛有些舒展。他就爱吃那山芋稀饭。想当年大跃进时期,一年到头不过几瓮粮食,日子怎么过?他就让劳力娘在家前屋后栽上山芋。那年,山芋成了家中的主粮,吃饱了,吃够了,吃伤了。劳力娘一见山芋头就大了。奇怪的是劳爷却对山芋充满感情,爱上了吃山芋。
河边。风大。翠花带着娃,看着劳爷。娃子忍不住打了个喷嚏,震天响,估计要感冒了。回吧,我再蹲蹲。劳爷舍不得土地,更舍不得孙子,便答应儿媳妇马上回。
劳爷停下手中的锄头,从口袋里摸了根烟点燃,吸了起来。
4.
那个晌午,劳爷的烟吸得时间可不短,一直到傍晚暴雨下了起来,劳爷才回来。这一回来,劳爷就病倒了。上了年纪的人了,淋了雨不生病才怪呢。高烧发到四十度,把劳爷的嘴皮都烧破了,像干枯的枝叶,煞白。当天夜里劳爷就被送去了县城医院,直到第三天,劳爷才完全清醒过来。
劳爷一醒就问儿子劳力,那块地推土机去了吗?庵棚在吗?那些大豆、山芋还有高粱长得怎样?干不干,别忘了浇水?劳爷连珠炮地问话,把众人吓得一跳。
好着呢!好着呢!爹,您就别操心了。二期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发,还有段时间才动工呢。劳力边把他扶坐起来,边发泄自己的不满,真是瞎操心,把自己操好就不错了。庄稼是你命啊?
劳爷挣扎着,从病床上坐起来,小兔崽子的,你叽咕什么啊?庄稼不是我命,恐怕离开庄稼就没有你这没良心的家伙?你个吃粮食不讲人话的。劳爷急速讲话,一口气上不来就胸闷气短了,半天才言语。他把老伴叫到身边,耳语道,劳力娘,我没事的,你去帮我看看那块地,啊?
劳力娘欲言又止,好,好,好。儿子劳力问娘,爹想干什么的?
劳力娘说,他不放心,叫我再去看看那块地上庄稼。你爹啊,哎,一辈子劳碌的命。劳力娘叹息道,脸上挂着泪走了出去。接着儿媳妇带着娃子从家里送饭来了。
儿媳妇指着爹对娃子说,叫爷爷,快叫爷爷!
娃子挣大着乌黑的眼睛,望着,爷爷,爷爷。
劳爷高兴地眯着眼睛,把孙子拉到跟前,你想吃什么啊?等爷爷病好了再给你买,啊?
孙子歪着头打量,谢谢爷爷。我要吃玉米棒。
劳爷听了孙子的话,更加开心了,搂住孙子的小嫩脸,不停亲道,乖乖,不愧是我孙子啊,比你爸强;看来爷爷的那块地没白种啊,再过一段时间,那玉米长熟就可以烧吃呢。
蹭、蹭、蹭,劳爷竟然从病床上下来了,对孙子说,走,回家看玉米去!
劳爷的病似乎好了很多。
5.
劳力娘去了那块地,走一路哭一路,很晚才回来。绿地旁,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、装潢垃圾等,小山似的包围着,一天比一天多,渐渐要淹没了这块地方;绿色的世界即将被白色恐怖统治着。在这越来越瘦弱的巴掌大田地上,喝足水、晒透阳光的玉米、大豆们依旧在晚风中摇曳着,碧绿着,鲜嫩着,丝毫没有感觉到末日的降临。
劳力娘一个人坐在地头哭。哭一气,想一气,想一气,哭一气。哭这块即将沦陷于城市的土地?还是相依几十年的劳爷?当然是劳爷。劳爷哪里知道,他得的不是感冒发烧的病,而是癌症后期了,估计离走的日子不远了。
劳爷在医院已经住了七八天了,答应孙子去看那块地,掰玉米棒子烧吃也没有实现。劳爷几次想去,不是被儿子、老伴劝住,就是医院的医生、护士不让。他纠缠过护士,哀求过医生,就一会,去地里立马就回来。不行。劳爷逼急了,就发脾气,我这不是为了孙子吗,答应带他吃玉米棒,还能食言?我就是想让他尝尝泥土刨出的粮食,到底吃下不?哎,医院哪里是穷人住得起啊?庄稼人,谁当他一回事?吃上几片药,打上几支针水,凑合一下就行了。庄稼人说,人是不能闲着的。闲着就会出毛病的。一到午忙三季,就没有庄稼人头疼发烧的。不是没病,而是选择挨挨就扛过去了。再说,一旦去医院,那地里的庄稼可咋办?生病不要紧,庄稼比命贵。劳爷只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爱睡觉了,有时想起都起不来,只觉得睡着好受点,虽然,这七八天没有睡过一次完整的觉。
准确地说,劳爷是睁着眼睛睡的。
儿媳妇翠花站在床前,爹,休息一会吧,别想着那块地,庄稼长得好着呢。劳爷轻声嗯了一声。孙子趴在爷爷的床头,爷爷,别急,等您病好了我们再去掰玉米。劳爷努力挣扎出微笑的样子,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劳力娘转过脸去,使劲地揩了几下眼角,也走到劳爷的身边。她拿着从市场里买来的豆角,举给劳爷看,老头子,你看,我们拾边地的豆角长这么大呢,快熟了。
劳爷见了,立马来了精神,可是吗?我说的,我种的庄稼还能差?。
这一见,劳爷一刻也坐不住了,吵着闹着要出去,要去看看那块地里的庄稼。谁也劝不了,只好从了劳爷的愿。
众人抬着担架出了医院。
6.
谁也不敢相信,劳爷一接触到泥土的气息,居然闭上眼睛睡着了,而且睡得那么香;更惊诧的在睡梦中嘴里唠叨着什么稻秧、大豆、高粱一类稼穑之事。
直到第二天黄昏,劳爷再次醒来,把众人吓得一大跳。
守在庄稼身边的劳爷精神着呢。他一咕噜爬了起来。有人惊呼“劳——劳爷您——”,劳爷已经走到玉米身边了。
劳爷拍了拍身上的尘土,清脆地咳嗽了几声,对劳力和众人说,大惊小怪什么,我不是好好的么。你们都回去吧。
众人皆诧异,怎么了?劳爷是回光返照,还是完全康复?怎么一踏上这地上,劳爷立马就鲜嫩着,抖擞着。
劳爷把目光停息在远处。远处,推土机、挖掘机,还有砖、石头、钢筋等建筑材料铺天盖地,脚手架也越长越高,把往昔的田野推出去好远好远。成片的树木也在疼痛的锯割中轰然倒下,微弱的疼痛声只会淹没在都市大海般的喧嚣声里。疼痛的消失的不止是这些树木,还有鸟儿、庄稼和村庄,甚至最后还有人。
劳爷黯然泪下,猛吸口气对众人吼道,还不走?我想和土地说说话??
劳力娘看着劳爷,眼泪花花!
劳力娘知道劳爷心事。找土地、庄稼说说话,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劳力娘记得有年夏季,从淮河上来的洪水,冲缺了河堤,淹没了村庄、草垛,还有大片大片的土地。原先葱茏翠绿的黄豆苗,洪水走后,留下孤独苗条的身影。年轻的劳爷欲哭无泪。贫穷的家境、贫瘠的原野。还有瘦弱的劳力娘和肩上哭泣的娃。劳爷在洪水走过的地方,在稀疏的庄稼丛中撒上绿豆种,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、薅草。早晨,劳爷扛把锄头和土地切切私语;黄昏,劳爷用镰刀和杂草纠缠厮磨。
劳力娘记得年轻的劳爷喜欢在黄昏的旷野里,引亢高歌,那拉魂腔似的牛号就从暮色里弥漫上来,荡漾在晚归的路上。
哎——哎呵呵——呦——哎呵呵——哎——哎呵呵——呦——哎呵——呵——夕阳一落满天霞照得南湖好庄稼芝麻地里好甜瓜……
声音苍凉、悲戚,开始低吟,渐渐敞开嗓门,逐渐嘹亮,盘旋在苍茫的原野深处;落日静止,倦鸟低飞,暮归的老牛也停下了脚步,凝神谛听。
7.
众人走远。
建筑工地上的机器声却近清晰地抵达劳爷的耳畔。挖掘机如一只巨大的钢铁老虎,摧以枯拉朽的气势吞噬着大地上的一切。日子一天天逼近,劳爷明白,不要多久,仅存的这块巴掌大的拾边地就会立马消失,永久地消失。
劳爷来到山芋身旁,伏下身子。山芋,我的好伙计啊……劳爷轻轻地抚摸着山芋汁液充盈的叶子,轻轻擦拭着叶子上的尘埃,泥痕擦不掉,劳爷就伸出衣袖,沾了点唾沫,轻柔地一擦,泥痕就去掉了,叶子显得更加嫩绿、更加生机勃勃。透过裸露的红色的山芋,眼前仿佛呈现出小山似的山芋堆。曾经,就是山芋充当家庭主粮,挺过那青黄不接的日子,让劳爷的一家从那个饥饿的年代里走出来。
一想着山芋马上就要被长高的楼群所代替,埋没在钢筋水泥结构的地下,暗天无日,劳爷泪眼又婆娑了。
山芋,我可对不住你啦?我没能很好地保护你,就是连这一点的土地,我都做不了主。老了,不中用啦,谁会在意你我的意见?人说,不能忘本,可是,现在的城里人,谁还记得当初农民的模样?一转眼,就把你我抛弃了,反过来还嫌弃我们呢,就像我那不孝的儿子劳力,小孬种的,不拿土地当好的,削尖脑袋,往城市里钻……
说着,劳爷来到了玉米身边。
阔大的玉米叶子在晚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劳爷说,老伙计,在和我说话吗?看得出你也不舍得脚下的土地啊。你看你抓着细碎的泥土死死不放呢。还记得风里雨里,我为你耕地、点种、锄禾、打药、施肥、薅草?干旱时,我和老伴还一瓢一瓢地给你浇水。你很体贴我啊,一到秋天,不惜与土地吵架,硬是给我送来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,黄亮亮的,挂在咱家的屋檐下,齐展展地守护着日子,吃玉米糊、嚼玉米饼,你劳苦功高哇,我几个娃子都是靠你考上了大学。
说着,劳爷来到了大豆的身边。
说着,劳爷来到了高粱的身旁。……
当儿子劳力找到劳爷的时候,大家发现劳爷躺在庄稼的中间,手中紧握着一穗玉米棒子,火红的缨子,映衬着劳爷脸上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 该帖已经同步到泗洪微博 古城泗洲的微博 该帖已经同步到泗洪微博 古城泗洲的微博 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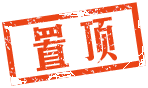
 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我爱大泗洪
( 苏ICP备2023057549号-1|
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我爱大泗洪
( 苏ICP备2023057549号-1|![]() 苏公网安备32132402000627号 )
苏公网安备32132402000627号 )